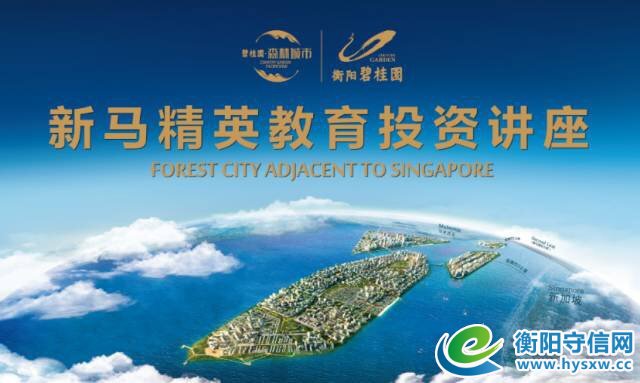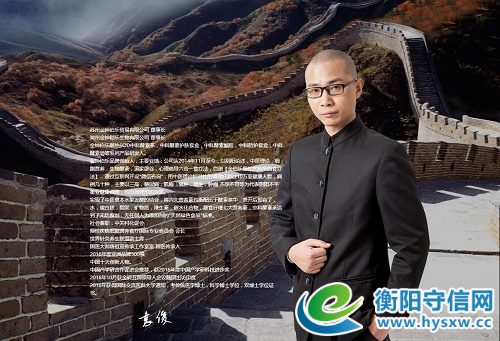八中故事汇| 辞山川
晚风悠悠荡荡,把我们吹出了最后一科的考场,也吹远了我们最热烈的高中三年。那风卷着六月的热意与试卷上萦绕的墨香,拂过那一间间熟悉的教室,拂过沐浴着金黄暮光的讲台和黑板,也吱呀呀吹开了记忆的大门。于是,那些曾立于讲台之上、以不同方式耕耘着我们心田的身影,便带着各自的光晕,次第清晰起来。
“我们的蒋亦丰同学总是爱写六朝骈文啊。”当记忆的流光漫溯进语文课堂,程雅琴老师温煦的声音仍回荡在耳畔。初入八中,我那尚显浮华的文风很快便引起了她的注意,而她总能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巧妙融入真诚的赞许之中,让人知其所短,却又如沐春风。于是,作文练习后的办公室里有了我求索的身影。从审题立意到文脉筋骨,从谋篇布局到思辨深度,她以近乎严苛的标准雕琢着文章的每一个层面,却也从不吝啬对我每一寸进步的由衷喝彩。程老师的魅力,便在这高标准严要求的师道,与春风化雨般温和滋养的师心间悄然生发——那是晚自习时办公室守候的明灯,是课堂上目光里的赞许和欣慰,是联考前对我们班“全省第一”的期待,更是考后出现在每位同学课桌上、那带着甜蜜慰藉的雪花酥。这雪花酥的滋味,早已超越了舌尖的甜润,而是悄然融入了我们文字的风骨,化作了岁月回甘的隽永印记。
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。对谢德斌老师的回忆,始于那一声声“多摸(琢磨)一下”的叮嘱里。面对他留下的难如登天的横格本作业,我们抓耳挠腮却也只能望洋兴叹;“大题只写个答案,你们的眼睛是天使之眼吗?你们的圆曲还没汝(入)门啊!”待讲评时,他常常捏着几本作业,恨铁不成钢地叹息,“罢了,谢老师今天就把这类题型的心法传授给你们!”在思维的困顿之谷与顿悟之巅里,他以体系为路,化妙法为阶,指引我们通向数学的佳境。作为执掌一班风帆的班主任,他总是最早踏着晨曦来到讲台,又最晚披着月光锁上办公室的门窗。他巡视的目光锐利如尺规,总能精准丈量出我们内心的起伏。还记得那个晚自习,他如寻常般踏入黑暗的教室,摇曳的烛光映衬着蛋糕,也温柔地映照着他惊讶的面庞。“谢老师,生日快乐!”伴着如潮的掌声,笑容如烛光般在他的脸上跃动。“谢谢你们了,同学们!愿你们的高考与人生,都像eˣ般无穷向上,都像坐标系一样宽广!”
而颜曾艳老师的声音总是在考试前涨潮。轻轻走过一排排课桌,她的目光四下搜寻着正复习英语的同学:“拿到试卷记得先扫一眼听力题目,阅读题记得写完就要涂答题卡;注意整张卷子的时间分配,两篇作文要留足50分钟!……”叮咛如细密针线,一针针缝补着我们粗疏的考试习惯。其实,颜老师的疆域远不止考前。一旦“This group,please”的火车开动,就算坐在最偏僻角落的同学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;“天呐,又发周报!”纵然哀嚎遍野,周报总能稳定地统治我们的一节自习;正午空旷的办公室里,天光如瀑,将她伏案批改作文的身姿拓印成寂静的剪影。说实话,我们曾厌烦过她拖堂的习惯,也痛恨那试卷的雪崩,更为自己因非衡水体而痛失作文高分而忿忿不平。但,直到真真切切地坐在高考考场,面对似曾相识的题目,那课堂上嘱咐的细节、字母圆润的弧度突然苏醒于笔尖,化作了成绩单上流光溢彩的分数——原来语言的精进不在顿悟,而在日日年年的练习中积累。她那异国音节的清韵,终成耳畔永恒的潮声。
若说前三位老师的形象都以温和儒雅见长,那么初看刘龙华老师,则觉迥然不同。犹记得高中第一节物理课,他阔步走进教室,在讲台侧站定,深邃的眼眸凝视着我们,开口道:“今后高中三年,你们的物理跟我混了。”配合上他棱角分明、不怒自威的脸,颇有些黑道大腕叱咤风云的霸气。但当你与他相处日久,便会发现那“江湖气”的铠甲下,掩不住的是滚烫的热忱与关怀。他的课堂满是生动的幽默,讲到关键处,手在白板上一划,“看,这两项火并掉了!”火并二字石破天惊,瞬间将抽象的公式推导具化为刀光剑影,引得满堂会心一笑。纵使偶尔嫌弃我们“物理水平太low了”,他的语气里也并无苛责,反而像老大看着不成器的小弟,鞭策之情溢于言表。一旦发现你的状态不对,即使不是我们班班主任,他也会在你踏进办公室时叫住你,问到:“最近怎么感觉你状态不对劲啊?”抽丝剥茧,循循善诱,三言两语便解开了我们心头的郁结。白炽灯的光晕照着他的面庞,那暖心的笑容竟透露着磐石般的可靠与坚毅。他以细密的关怀与江湖气的幽默,把我们“罩”过了这与物理苦斗、兵荒马乱的三年。
对单慧芳老师的回忆,则绕不开奶茶的细腻甜香。“喏,化学考年级第一的奖励,趁热喝吧!”她把升腾着诱人香气的奶茶轻轻放到我面前,镜片后闪动着狡黠而欣慰的笑意。彼时,我正醉心于化学竞赛的求索,对课内的化学内容自然不屑一顾。她发现了我的偏航,却不愿打击我的骄傲,而是抛出了一个诱人的邀约:“不听我课,行啊!只要你化学能考年级第一,我不仅不说你,还奖励你一杯奶茶!”这杯奶茶从此成为了天平上的砝码,一端压着我竞赛生的骄矜,另一端坠着她的期待。为完成约定,我只得重新潜入那被她梳理得澄澈通透的教材汪洋。于是,先前被忽视的基础知识悄然浮现,未曾关注的实验内容被烙印入脑海之中。“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。”此时再回望一路来采撷的化学知识,我对这门学科反而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每当我摩挲着写满反应的化学笔记本,那杯奶茶的温热仿佛就隐隐传来。那杯壁上水珠滑落的奶茶杯,原是她精心设计的思维冷凝管——它冷却了浮躁的蒸汽,让我在回归基础的蒸馏中,重新提纯化学最本真的液晶。
而代明龙老师则是讲台上的特立独行者。他的课堂常常超越教材的边界,直探生物更高层次的幽微:课本无法回答DNA复制时前导链的缩短,他便以端粒酶修补我们的困惑;教材没有解释呼吸作用时能量的流动,他就用电子传递链消解考试的疑难。而他最令我们拥护的一点,便是那如条件反射般精准的下课时间——就算题目念到一半,只要下课铃声响起,“下课”二字必定脱口而出,如同手术刀般将课堂精准截断。然而,铃声催他离场,却难释未解之疑问,面对簇拥而上询问问题的同学,他驻足而立,走廊转角皆成答疑之讲台。他细细聆听同学的疑惑,眉头紧皱而又舒展,三言两语便道出了问题的肯綮,还未解答就让问者茅塞顿开。纵使上课铃声迫近,他仍稳立于问题的漩涡之中,直至同学们的最后一丝困惑涣然消释。他看似吝惜上课分秒,却慷慨地挥霍课间的光阴,以守时的表壳,包裹着为求知者无限延宕的传道解惑之心。
“教育之于心灵,犹如雕刻之于大理石。” 跌跌撞撞地走过这三年,我们的灵魂里早已留存了老师们不可磨灭的烙印。那是齐读《离骚》时字里行间激荡的浩然正气,那是公式推导时一步不落的理性与严谨,那还是……那还是他们用行动向我们展示的伟大的心灵。他们善良,他们热忱,他们永远任劳任怨,他们以从高从严求真求美的态度,一丝不苟地描绘着学生们未来的蓝图,打磨着孩子们浑金璞玉般的心。他们甘做那闻一多诗里的红烛,陶然燃烧着红艳艳的心血,莫问收获,但问耕耘。
下考铃声响起,我们如潮水般涌出教室,奔向霞光绚烂的广场,脚步踏响大地,我们奔向山长水阔的前程。蓦然回首,记忆里的老师们正不断远去,渐渐模糊成一片温润的光影。他们站在一起,宛如一片无言的山脉,默默托举着我们这些奔腾的溪流。如今,溪流已告别山川,奔赴前方浩瀚的大海,可它们中的每一滴水,都忘不了那在群山间激情奔涌的岁月;而那日渐遥远的山川,就成了生命中不变的怀想,记忆里永久的地平。